女性战地记者——不一样的战争观察者

一.她们的身影
虽然在战争题材的电影和书籍中经常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但几十年来,她们一直在前线报道战争。最近的俄乌战争报道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女性战地记者,拉丽莎·沃德(larissa Ward)就是其中之一。她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凸显了女性记者的技巧和勇气,这些事实反驳了女性不应该报道战斗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们的存在甚至改变了战争报道的性质。

沃德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铁站作现场报道
这些女性战地记者的报道不仅涵盖了一般的战争策略,同样也衡量了战争带来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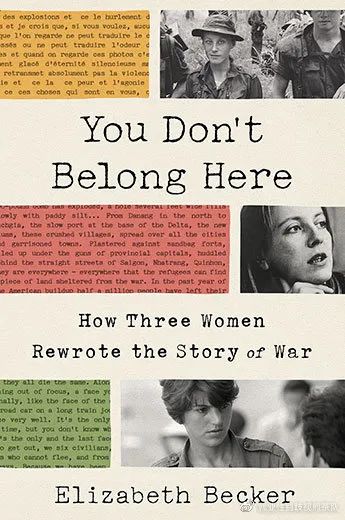
《你不属于这里》封面
《你不属于这里》(You Don’t Belong Here)是一本出版于2021年的书,介绍了三位报道越南战争的先锋女性,作者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为上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战地记者)说,“毫无疑问,我认为这种报道更人性化,着眼于战争中人性的一面。”

伊丽莎白·贝克尔
贝克尔认为,美国的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澳大利亚的凯特·韦伯(Kate Webb)和法国的凯瑟琳·勒罗伊(Catherine Leroy)奠定了现代战争报道的基础。她们自费来到东南亚,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什么新闻工作经验,凭借大胆和创新打破了男性对战争报道的控制。
1973年,菲茨杰拉德凭借《湖中之火:越南人和在越南的美国人》(Fire in the Lake: the Vietnam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荣誉。2017年,她的作品《福音派:塑造美国的斗争》(the Evangelicals: the Struggle to Shape America)入围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

左起:记者凯特韦伯,1968 年;记者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973 年 5 月 1 日;在南越联合城行动期间,摄影师 Catherine Leroy 即将与第 173 空降师一起跳伞,1967 年 2 月 22 日。
在越战前的20世纪主要冲突中,包括二战和朝鲜战争,女性面临着军事障碍和职业偏见。著名的记者兼小说家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在二战诺曼底登陆法国时,和其他女记者被拒绝进入前线采访,于是她就躲进了一艘医院船,报道诺曼底登陆的情况。

玛莎·盖尔霍恩,《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在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担任战地记者长达五十年。
曾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在1950年战争爆发时,曾被一名美国军官命令离开朝鲜,她最终通过向麦克阿瑟将军上诉,才成功留在前线。1951年,希金斯因其广受赞誉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评审团指出,她“由于是女性,因此有权获得特殊考虑,因为她必须在不寻常的危险下工作”。

玛格丽特·希金斯,曾亲赴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中采访,因为其在韩国深入战场的报导和成就而声名大噪,并成为普利策奖的第一位女性得主。
后来,女性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中表现出色,包括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伊迪丝·M·莱德尔(Edith M. Lederer),她是第一个被派到那里全职工作的女性,现在是美联社驻联合国首席记者。在随后的各种战争中,女性战地记者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包括乌克兰——那里的报纸、网站和其他媒体都以女性记者为代表,即使她们的名字不是因在镜头前的报道而为人所知。

伊迪丝·M·莱德尔

登比·福塞特
伊迪丝·M·莱德尔是美联社第一个被指派全职为越南工作的女性,现为美联社驻联合国首席记者。她回忆起1972年到越南时的情景,当时她会见了包括登比·福塞特(Denby Fawcett)在内的前任记者,1966年开始为《火奴鲁鲁广告报》报道越南战争的福塞特和“其他几位女性成功地打破了障碍,让女性在战场上与男性平等。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莱德尔说。
女性对战争报道本身有影响吗?
“当然,”莱德勒女士说。“我在越南写了一些我不一定认为我的男同事会写的故事。......他们对战争的发展方式更感兴趣,当然这是我们之所以来这里的原因。”但她也花时间报道了一家爆炸和枪击受害者包括儿童做整形手术的医院,当她手里拿着气球来到医院的时候,“各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高兴地大喊大叫,令我大为震惊。”
新一代记者正在报道乌克兰,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中有很多女性记者。在伦敦出生的CNN首席国际主播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Christiane Amanpour)说,战争报道是“一种使命感,一种目的感,一种能够讲述一个故事的感觉”。“看起来,女性真的非常擅长这个。”

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
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CBS新闻驻乌克兰记者霍利·威廉姆斯(Holly Williams)说。“我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你不讲述女性的故事,你就会错过至少一半的情况,”生于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说。她曾报道过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冲突,并为BBC新闻(BBC News)工作。

霍利·威廉姆斯
沃德说,“女性对战争的看法通常是不同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并不是很多报道的重点,”她努力将“故事背后的人性,生活在战区的普通人的经历”融入其中。对我来说,这和军事部分一样重要。”正如ABC新闻资深记者玛莎·拉达兹(Martha Raddatz)等人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许多男同事也贡献了细致入微的报道。但她回忆说,在不久以前,男人往往“喜欢设备,喜欢飞机”。

玛莎·拉达兹
沃德和其他女记者向她们的前辈致敬,包括菲茨杰拉德和盖尔霍恩,她们的报道范围从二战一直延伸到1989-90年美国入侵巴拿马。他们还赞扬了最近的包括阿曼普在内的先驱者。
阿曼普几十年来的冲突报道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随后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以及在欧洲东南部,1992年至1996年波黑战争期间致命的萨拉热窝围攻。“我想,女性驻外记者保持少数的状况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就结束了,”阿曼普尔说。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中,记者“突然成了一个非常适合女性的职业”。
但薪酬方面还没有实现平等。沃德说道,在所有的新闻工作中性别平等也远未实现。她说,越来越多的电视女记者掩盖了“总体上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别忘了,镜头前的人是一个人。在电视节目中,有四个人拿着相机,站在相机后面,其中大多数还是男性。”
在整个新闻业中,即使在不断变化的媒体行业中,男性仍比女性拥有数量上的优势。根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2020年的报告《新闻中缺失的女性视角》,几项多国研究表明,尽管取得了进步,但“全球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记者都是男性”。
阿曼普尔说,女记者在非民主国家和一些地区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她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然在伊斯兰世界和其他我称之为父权制的地区,女性记者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女性在乌克兰的报道是建立在传统角色和期望的背景下的,妇女和儿童被允许逃离战争的暴力,而男性则被要求留下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约纳特·弗林
福克斯新闻频道驻耶路撒冷的高级制片人约纳特·弗林(Yonat Friling)曾在乌克兰与记者特雷·英斯特(Trey Yingst)共事,她知道人们的态度会有多大差异。2004年,她在以色列一家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工作,当时她要求老板把她调任为现场制片人。但“他告诉我,‘这是男人的工作’。”
二.战争报道中的性别视角非常重要
1.出于“需要被保护”的歧视
作为记者出现在武装冲突地区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虽然大部分殉职的战地记者都是男性,他们的女性同僚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显然得到了更多关注。
“战争和冲突会特别加强父权结构,而这一点也会影响身处其中的战地记者们。比如,女战地记者们经常发现,她们不能像男记者一样参与对自身风险的安全评估。”Hoiby说。她和另外一名教授采访了七个国家四个大洲的记者和编辑。
平均每周都会有一名记者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被杀害。媒体工作者经常面对暴力,恐吓,欺骗,非法逮捕,甚至绑架。这些案例很少被调查,而加害者往往不受惩罚。“大部分受访记者和编辑都提到,战地报道正变得更危险。战争更加复杂,在前线分辨冲突双方越来越难。”Hoiby说。
更糟的是,战地记者大多失去了他们的中立身份。“战地记者们正在成为特别的攻击目标。在过去,记者还可以利用他们的中立身份保护自己,甚至和冲突双方都实现沟通。但今天更多的记者选择低调不出头。”
无论如何,报道战争和冲突仍然是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而确实有许多战地记者不顾自身风险,活跃在一线。但女性记者往往发现自己被男性同事们替代,无法获得同等的工作机会。
“当然有一些情况,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成为暴力的目标。这不仅因为她们的记者身份,更因为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挑战传统性别分工。”Hoiby说,“在2011年报道开罗解放广场集会时,媒体组织‘记者无国界’官方发布了警告,特别要求各媒体机构保护它们的女性前线记者。他们发现在解放广场上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的有组织的性骚扰和性暴力。”

2012年11月27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者和帐篷。(美国之音威克斯拍摄)
但Hoiby认为,我们必须提出问题:既然每年被杀害的记者中90%都是男性,为什么这类警告和特殊保护总是面向女记者?男记者也需要特殊保护,更何况针对男性记者的性暴力并不少见,只是没有人讨论。
巴基斯坦男记者Cheema就曾经在2010年的一次报道中被绑架,殴打以及遭受性侵。2008年,菲律宾的三名电视记者也曾被反叛组织绑架九天,其中两人为男性。在此之后,菲律宾媒体机构开始严控进入战区的女记者,三人中的女性也被多次问及是否受到性暴力,但从未有人关注这两名被绑架的男记者。
“虽然讨论性暴力无论对谁来说都很困难,但对于男性来说这是更大的禁忌。如果有记者讨论性暴力问题,他们会被视为软弱,作为战地记者不够格。”
Hoiby的研究也发现,相对男记者,女战地记者往往对风险有更多意识,也会做更多准备工作,比如更方便和更贴近当地习俗的着装和行为。“她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排除,为什么不能像男同事一样评估自己的安全,选择自己的目的地,做自己的报道。”
2.女性独特的报道视角
女性记者应当与男性有同等的工作机会,哪怕是危险的工作。但战地女记者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平等的机会。“女记者报道战争和冲突的视角非常重要。比如,她们经常有男性记者无法获取的资源,尤其在存在性别隔离的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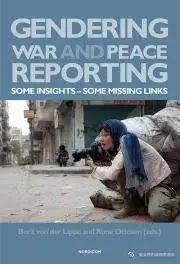
Hoiby的文章是一部人类学研究著作的一部分。这本书名为《战争与和平报道中的性别,一些洞见——一些缺失的环节》(Gendering War And Peace Reporting. Some Insights – Some Missing Links)。
男性和女性在媒体对战争和冲突的报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对和平进程的报道中又是如何?作为男性或者女性战地记者,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在战争和性别报道中,都有哪些常见的刻板印象?如何挑战这些刻板印象?
“虽然在西方,我们讨论性别的方式已经改善了许多,但在报道战争中的男性和女性时,仍然存在大量的本质主义报道。”本书的作者之一von der Lippe说。“比如穆斯林女性,几乎完全被刻画成被动的受害者,她们在报道中从来不会是高效率的行动者。”“库尔德女性一直在和男性并肩战斗,但在我们的报道中,她们仍然只被当作一种‘异国情调’,而非解放战士。”
虽然她同意Hoiby的观点,即女记者通常有不同于男记者的视角和采访对象,但von der Lippe并不认为女记者的存在会自动改善媒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她认为,虽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批判女性如何在本国的
本国的历史叙事中被排除,但他们在报道其他地区时却沿用了同样的方式。
三.战地记者个人故事——玛丽科尔文:“她通过个人的痛苦阐明了战争的代价”
数年前玛丽·科尔文死于叙利亚政府袭击,在绝望、被围困的霍姆斯镇,她一直是英国战地记者的元老,尽管她可能会讨厌这个词。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撰稿,科尔文的工作确实实现了大多数记者开始职业生涯时的梦想——通过见证来拯救生命。

2001年,她的一只眼睛被斯里兰卡的火箭推进榴弹弄瞎了,此后她就戴上了一只眼罩,这眼罩成为了她的标志。霍姆斯(叙利亚城市)的袭击旨在让她噤声,并阻止其他记者追随她的脚步,但今年秋天,随着残酷的内战蹒跚走向第八个年头,她重新出现在屏幕上、报纸上和书架上。
好莱坞传记片《私人战争》、严肃的传记电影《极限特工》和有相当影响力的纪录片《火线之下》都在几周内相继上映。就在几个月前,一部略带虚构色彩的法国电影上映,该片也探讨了她的生活和工作。56岁的她因其工作受到极大的尊重,但她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这些对她生活的重新演绎是对她的遗产的非凡致敬。
下令屠杀她的人认为,在她的祖国美国或她的第二故乡英国,失去一名记者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悲剧,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但尽管新闻业通常不受尊重,记者与律师和政客一起,在“最不受信任的职业”名单中垫底,但前往战争或灾难现场的记者仍有一种持久的魅力——不是奉命作战或提供援助,而是作为战争行为的观察者。

这种持久的魅力可能来自于对勇气的尊重和好奇。科尔文对自己的恐惧毫不在意。“勇敢就是不害怕恐惧本身,”她曾经说。但毫无疑问,她会去别人不愿去的地方,跨越国界,留在战区,即使那些在有战区有过深刻过往的人也绝不会想要留下。
1999 年,当她和另外两名妇女选择留在东帝汶被围困的难民大院时——外交官和其他大多数记者因害怕暴徒而离开——她可以从字面上声称让男人、女人和儿童活着(尽管她没有自吹自擂,而是让别人来记录她的成就:报纸的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她的勇气拯救了1,500 人”)。
西方人或许从未远离战争的现实。随着最后一代二战幸存者和退伍军人步入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军队现在已经是一支小型的专业部队,许多英国人并不知道有谁曾忍受过沉闷而可怕的战争的日常折磨。透过屏幕来看,暴力既引人注目,又虚无缥缈。

而且她是一个女人。女性作为士兵、记者或医务人员上战场,有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人们好奇是什么吸引她们来到这个男性占绝对优势的世界,以及她们如何在那里生活。任何一个仅仅去了一个稍微不稳定的地方就被诱导性问题刺痛的女人都知道这一点。科尔文对此了如指掌,并加以利用。当她和难民们一起在东帝汶蹲着的时候,编辑们问她那些男记者发生了什么事,她几乎只是耸耸肩,不接电话。“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制造男人了,”她回答说。
像许多追随她的女记者一样,科尔文利用厌女症完成了一些她最好的作品。在女性被视为无能为力、无足轻重的地方,男性往往无法将女性记者视为真正的对手,并给予她们相对自由的通行证。在公开场合,科尔文几乎没有时间专门关注女权主义,她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著名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的一句话:“女权主义者在指责我”。但私下里,她敏锐地意识到,为了获得同样的机会,人们总是要求她比男性更出色。她想了很多她的报道和主导这一领域的男性的报道之间的差异——尽管女性战地记者的数量正在增加,但现在男性仍占主导。

她的报道能够如此有力的一个原因是,它避开了与该行业大男子主义形象相关的许多特征。她对军事装备没有兴趣,对挑选枪支、直升机或火炮也没有兴趣。相反,她关注的是金属撞击人体时会发生什么,被围困、饥饿或逃离的妇女和儿童的命运。她没有从难民营的幸存者那里收集经常被认为是“软弱”的故事,而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记录冲突中心的恐怖。“也许我们觉得有必要更多地试验一下,看看我们能承受多少,幸存几次,”她在谈到女记者时写道。
她最好的作品通过个人的痛苦来揭示战争的代价:一个青少年在试图跑进狙击手的巷子去找食物时被枪杀,围绕着一把土的细节,展现她的小金耳环,她紧握的拳头,以及伴随的死亡痛苦。
当然,由于目睹了如此多的冲突,科尔文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创伤,她的个人生活常常痛苦而混乱,而她的早逝则是一个悲剧。但她的生活并不是悲惨的。科尔文很有魅力,美丽又风趣,她在工作中找到了目标和意义,并为自己的成功和声誉感到自豪。
传记片里有一句台词特别让人印象深刻,那是对科尔文选择的生活的某种背叛。科尔文的扮演者罗莎蒙德·派克说,“也许我会喜欢更正常的生活。也许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据她所有的朋友说,科尔文正过着她自己选择的生活。在巨大的野心和天赋的驱使下,她逃离了她在小镇上长大的那种令人乏味的正常生活,进入了一个充满权力、魅力和名望的世界。她乐于成为前线最大胆的人,派对上最具魅力的人。
(来源:sciencenorway,theguardian,The ChristianScienceMonitor,vogue;翻译:小庄,Karen)

